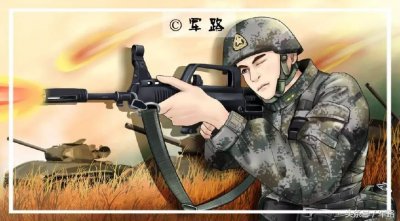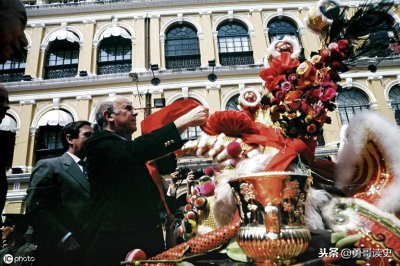荔枝红了之《荔枝春》
荔枝红了之《荔枝春》

荔枝春
1
踏入五月,立夏骤至,空气立时闷热粘稠起来。街头巷尾出现红荔丽影,“荔枝春”又来了!
打电话:妈,阿姨摘荔枝了吗?
妈笑:阿舅也打电话问。
又说,舅最馋荔枝,当饭吃,一次能吃一箩筐。
曾为龙眼写过一篇《龙眼春》,吃过的荔枝比龙眼多,以箩筐计,自然欠荔枝一篇《荔枝春》。食客们或者只知“龙眼”“荔枝”,未必懂“龙眼春”“荔枝春”,我曾疑惑果农口中的“春”,是不是这个“春”。想想又觉得真好,也不去深究。
阿姨家有荔枝园。十多年前,承包山岭上丢荒的一片荔枝林,辛苦经营,表弟阿骄专注用心,学得一手荔枝管理技术,是荔枝园园长,长年扑在荔枝园,荔枝管理到家,年年荔枝都比旁人家长得好。这些年,每逢荔枝春,我们都有“阿姨牌荔枝”供应,也带孩子们去荔枝园摘荔枝,在红荔累累的树底下畅怀大啖……是不是挺美?
可是,我打了一个罢工电话:再不去摘荔枝了!
有好几年,年年带孩子们去阿姨家的荔枝园摘荔枝,最重要的一件事,要把刚摘下的最新鲜的荔枝,打包寄给外地的妹妹。每到荔枝春,妈就惦记着。
一颗荔枝一把汗!当半天“游客”我们已受不了,而身为荔农,阿姨一家整整一个多月,浸泡在汗水的河流里……阿姨、姨丈,三个成家的表弟们,带着他们的媳妇、孩子,以荔枝园为家,早出晚归。阿骄园长还得留守荔枝园,住临时搭建的工棚,值夜。每天雇请数十余个工人干活。摘荔枝、整荔枝、打包装……姨丈和三个表弟忙前忙后,还亲自上树摘荔枝。头戴破草帽、身着旧衣衫,身上脸上汗水长流,“像个乞吃佬”,表弟们自嘲。阿姨管做饭,后勤部长,带领媳妇们在荔枝园简陋的灶台前,切切洗洗,又炒又煮。
妈虽一把年纪了,手脚却轻快,阿姨人手紧,被特邀来帮忙做饭,阿姨照给工资。我们心疼妈,不情愿,可没办法,妈还是年年去当荔枝工。阿姨姨丈已年近古稀,黑黑瘦瘦,尤其阿姨,长年辛苦,比妈还显老。听妈说,阿姨每年为荔枝喷农药除虫,不止一次晕倒在闷热不透风的荔枝园。
今年是荔枝大年,阿姨家的荔枝大丰收,“荔枝春”又要忙得够呛。年岁不饶人,妈已年近八旬,经大家力阻,应承不再去荔枝园帮工,可是晚上打电话,妈第一句是叫回家拿荔枝,第二句才小声说,今天去荔枝园了……阿姨要救急,不去不行。
妈搭摩托车去。路坑坑洼洼,路边一座垃圾场,垃圾堆成山,上空大鸟徘徊盘旋,黑乌乌,不像蝙蝠,但像蝙蝠一样阴郁。阿姨家的荔枝园,在远远的山岭上。
妈从荔枝园捡回半箩筐“荔枝谷”,收购打包剩下的一颗颗荔枝,荔枝好好的,没人要的话,表弟们就一箩一箩地往园边倒掉。妈说,馋荔枝的阿舅,每到荔枝春,捡荔枝谷当饭吃。
2
盛夏酷暑,带画家们去根子贡园采风写生,事隔多年,再次走进贡园,一个历史悠远的古荔枝园,树龄过千数百年的比比皆是。
贡园里一些名树已有主,被人早早买下了“树花”。那棵树龄1300年的“荔王”,去年130万元给拍下,今年,“千手观音”拍卖价创新高,138万元。树已摘果,却仍然吸引荔客们往来如梭,在树下合影,瞻仰。贡园里的荔枝大多未采摘,老树挂新红,正是观赏好时候,可现买现吃现寄。远近荔农把贡园当作卖场,三三两两在树下摆摊,簸箕箩筐装满荔枝,吆喝售卖。说是现摘现卖,是贡园的荔枝。荔客们笑笑,半信半疑。一位老伯光着膀子,肌肤呈古铜光泽,面前几箩筐荔枝,热情叫喊:试试,好吃再买。坐下来试几颗,真甜。跟老拍聊天,老伯75岁了,说旁边这些都是他们家的荔枝树,荔枝就是树上摘的。是不是没关系,好吃就行。来回品尝多家(惭愧,白吃占便宜了),回头来帮衬老伯,买些寄给外地的朋友。
一棵名叫“天女散花”的古荔枝,树龄500年,被人花3万元包下,正在采摘。一架长梯直插高空,两个身影站立高梯,在树端摘荔枝,惊险如玩杂技。树下有人正在整理摘下的荔枝。500年的古荔枝是什么味道?厚着脸皮走近去讨颗来试试,舌间滚过的甜,500岁了,真甜……
树上在摘荔枝,不时啪地掉下几颗甚至整整一串,果真“天女散花”了。我们干脆坐在树下一块石墩上,静候“天女散花”,果真捡了便宜,500年的老荔枝不时啪啪地往下掉……500年的甜,真甜,边吃边感慨。
我们带来的画家们无暇品尝荔枝,冒着暑热,在古荔枝前一坐就半天,沉醉于线条与色彩的世界里。沧桑古荔点缀新红,在他们笔下获得另一种生命——艺术。
我去寻“廿四担”——贡园里一棵1300年的古荔枝树,果还没采摘,也不知有人买下没。感到遗憾,荔红时节,它等来无数荔客,却没有等来它精神上的知音。去岁深秋,著名画家陈金章来贡园采风,老人家被枝干苍茫遒劲的“廿四担”深深迷住,坐在树下,一画就半天。原计划下午有另外行程,年过九旬的陈老创作激情上来,却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任性,嚷着还要继续画“廿四担”。下午,老人家又坐在树下,一笔一划作画,身边围满本地慕名而来的众多画家和美术爱好者,新闻记者拍照采访。老人家却丝毫不为外界所动,全然沉醉在他的艺术世界里,满头银发闪闪发光,这一幕让我感动,铭记于心。
黄昏将临,陈老不得不收起画笔,意犹未尽地感慨,下次再来画,而且——他又像个孩子般天真:下次要静静地画,不要有人围在身边才好。
陈老回去后,根据写生作品精心创作出一幅《盛唐嘉木》,赠予茂名,为茂名荔枝,为他的家乡留下珍贵的艺术作品。
陈老年事已高,坚持锻炼身体,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心静手不颤,一支画笔从容淡定。他何尝不是一棵“廿四担”,枝干沧桑,却年年产出丰硕新果。祝陈老艺术之树长青,期待他有一天,能再回家乡画“廿四担”。 “廿四担”也在等他,千年遇一回的画家。
3
下午带画家们到另一个荔枝园写生。遇见几个女孩子举着手机自拍杆在荔枝林间直播卖荔枝。眼下“荔枝春”,荔枝成网红了。今年兴起直播卖荔枝,地方长官们纷纷上直播间卖荔枝,朋友圈天天刷屏,让人感慨,想起一曲经典粤曲《卖荔枝》:“卖荔枝——”一声长腔,乐韵飘扬,尔今古曲新唱,何愁荔枝卖不动?
荔枝有大小年,小年产量少,价高,大年产量大,价低,大年小年荔农无不喜忧参半,提着心。丰收却价贱伤农的事时有发生。记得有一年荔枝大年,满山荔枝挂果累累,最后销量却一路下跌,满树红荔摘也不是,不摘也不是。那一年,妈说起阿姨家的荔枝,直叹气。
阿姨家辛苦经营荔枝园十余载,起起伏伏,没见发荔枝大财,所幸维持了一大家子生活。一大家人挤一屋,儿子们都已成家立室,姨丈主政,用荔枝园的收入,为三个儿子在旧屋前各建一栋楼房,建了几年,还没建好入住。
今年荔枝春后,希望阿姨家能住上荔枝楼。我等着喝荔枝楼的喜酒——这酒,自然是荔枝“酿”出的酒,十年佳酿,该成了。
标签: